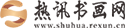李保田。
李保田,1946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国家一级演员。早年进入徐州地区梆子剧团学演丑角,曾任徐州地区文工团副团长。曾参演《人鬼情》《菊豆》《有话好好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马背上的法庭》等电影;《宰相刘罗锅》《神医喜来乐》《王保长新篇》《跃龙门》《巡城御史鬼难缠》《警察李“酒瓶”》《丑角爸爸》等电视剧。曾获金鸡、百花、金鹰、飞天、华表、中国电视终身成就等多个奖项。
 (资料图)
(资料图)
岁月是刻刀,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
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
每当我失望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上苍的目光在深切
专注地对我凝视,那正是他最钟爱我的一刻。
一
小时候,我并不是个灵秀聪明的孩子。母亲说我曾经胖而好玩、憨态可掬。贪玩好奇自不必说,这是小男孩的常情,却透不出日后离家出走、多年流浪的征兆端倪。
我五岁那年,厌烦了幼儿园的单调乏味,趁人不备,一溜烟儿跑到了离家不远的街上,东游西逛,饱看街景。那是个星期天,我头一次觉得没人管真好。
逛累了我就蹲在路边看那些大孩子玩儿弹球。玲珑剔透的球儿在地上美妙地滚动,我两眼直直地盯住那些尤物,却不料幼儿园、父亲单位、家里上上下下早已沸反盈天。天渐渐黑了,我浑然不觉。突然有人从背后狠踹了我一脚——是父亲,他暴怒地揪住我的耳朵,将我从地上拎起来。
当晚回到幼儿园,所有人不约而同从小床上坐起来,猫头鹰一般雪亮的眼睛怒视我。一霎时,我发觉自己第一次成为异类,成为众矢之的。平时藏在枕头下的小玩意儿全都不翼而飞,被那些满腔正义的小朋友瓜分掠夺了去。从那时起我开始纳闷儿,为什么凡人总把自以为稀罕宝贵的小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大概是把它们看得和自己的脑袋一样重要,需时时挨着,甚至还要带进梦里去。
那时我就很有特立独行的气质,极少与别人一起玩,这种自我意识在家里,尤其在父亲面前更是频频受挫。
父亲原本不是平和的性子,我加诸弟弟们的“暴行”常令他愤怒难耐。他又是彻头彻尾的旧式父亲,陶醉于多子多福的虚荣。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着孩子们上街,左手领着,右手抱着,身前围着,身后跟着,举家出动,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父亲脸上时常洋溢着骄傲的光彩,引人羡慕。而我的顽劣却常使父亲的自豪大打折扣,我被规劝、责骂、哄骗着跟他们出去,却不是超前二十米,就是落后二十米。
小学四年级结束时,我数学不及格,补考再次不及格,便留级。父亲说:“行,不给你买书了,用你的旧书吧。”我上哪找旧书去?课本都烂了,都让我撕咬成椭圆形的了,上面还画了好多的刀枪剑戟、武侠人物,课文内容都不全了,这使我比同学们矮了三分。因为留级,我在班里面比别人大一岁,个头比别人高一截,这可不是鹤立鸡群的感觉,而是羊群里出了一头驴的感觉,又让我觉得矮人三分。严重的自卑心理让我更没有心思好好学习了。
到了晚上,我就在剧场门口混,捡中途退场的观众的票根,我进去再看最后的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回到家十点左右,就睡了。那时候我母亲上补习班学文化,这个时间还没回家。就这样疏于管理又混了一年半,我终于混不下去了。
二
小学六年级那年的冬天,江苏省戏曲学校与江苏省文化干校来徐州招生。我背着父亲,领了一个弟弟去报名。
考试的时候,我竟然表演得活灵活现、活泼乖巧。我和弟弟很快都接到了录取通知。通知上要求2月24日晚上大家集合一起坐火车去南京。
我终于嗫嚅着告诉父亲我要去学戏,不再念书了。父亲一如想象中的大怒,暴打了我一顿。父亲是农民的儿子,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来在地方做干部。在父亲心目中,求学上进才是正道,跟着一群民间盲流当戏子,实在丢人现眼,有辱门风。他是老革命,不愿意我以唱戏为职业。我就拿着一大沓电影票去电影院待着,没有场次看了,就满街溜达。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父亲母亲就只好放行让我去戏校。
离集合的日子还有一天,我兜里揣着父亲给我们弟兄买的电影月票,在街上晃荡。一天下来,看了四五场电影,最喜欢的那部《大闹天宫》,我已经倒背如流,又看了一遍。第二天,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离开家,到南京去了。那是1960年,我13岁。
至今我仍不能确定,去学戏和在学校里念书,到底哪个会更有利于我的后来。
南京的日子全不如想象中的多姿多彩。我原本喜欢京剧,现在却要学柳子戏。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子戏乃是一个濒临失传的民间剧种。戏班里的师傅来源于民间,从没有进过科班,也就是高级戏迷、票友的水平。当我表达了想学京剧的愿望时,团里的人有些愤怒地说:“这孩子竟然看不起我们的柳子戏!”
我终究没能学唱京剧,却留下“小看柳子戏”印象。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学“丑”行。戏台上“丑角”机智、活泼、滑稽、俏皮,讨人喜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一直渴望讨人喜欢才选择了学“丑”。我的师哥当时已经二十岁,是团里的青年演员,自从我报了学“丑”行,他便视我为挑战者。
不久母亲到南京出差来看我,她流着泪劝我回去念书,我拒绝了,心里却几乎承受不住母亲的伤心流泪。母亲将一块绣着小花的白手绢给了我,我一直将它视作温馨母爱的象征,后来这块手绢成了我师哥一条裤子上的裤兜胆。
两个月后,我们从南京来到徐州郊区的乡下,那一阵忽然想家想得不行,于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硬着头皮回了家。
记得父亲的第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被剧团刷下来,回家上学还来得及”。父亲知道戏班里的学员需试用三个月才成为正式学员,这是劝我回心转意、“弃暗投明”的最后机会。
我一直闷头不语,父亲似乎心中不忍,给了我两块钱,叫我带上两个弟弟去看电影。街上没有电影可看,想起兜里的两块钱,我灵机一动,对弟弟们说:“你们回家吧,我直接回团去。”
那已是饥饿的年代,疲劳不堪的练功和稀少的饭食使我无法拒绝两块钱的巨大诱惑,我将钱花得精光,买了久违的几种零食,高高兴兴地回团。
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在团里吃过早饭,我领了一天的粮食——两个馒头,装在提兜里回到家。父亲不在,我暗自侥幸大家都没有提及那两块钱。然而父亲回来后,劈头就问:“那两块钱呢?”我慌了,却不知如何对答。“你那两块钱呢?”父亲又问。我真想告诉他自己怎样花了那两块钱,但那对于我是很难堪的事,于是我不甘示弱地说:“我以后还给你就是。”父亲暴跳如雷,抬脚便踢,我撒腿就跑,两个馒头忘在了家里,我身无分文。
从此一直到父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
我不喜欢社交,比较孤僻,这跟性格有关,而孤僻的人一般比较自卑,比较羞涩。我成长的剧团环境,加重了我孤僻、自卑,又自负的倾向。
问题出在全团成员与我的关系上。1960年我进入剧团,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来的孩子在困难时期能给老师送点家里捎来的东西,我什么都送不了。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几乎与家里断绝了关系,所以我无法从家里拿东西送给老师,自己更没有钱买东西。
夏天来了,我在这个充满敌意被人奚落的氛围里却有一件令乡下孩子眼馋的好东西——一顶雪白的单人蚊帐,那是我从家带来的。师哥说:“我来挂蚊帐。”于是我的好东西就成了他的。这并没有使我怨愤不平,因为尊敬师长是戏班的规矩,我自然应无私奉献。况且师哥大我七岁,对他依顺似乎天经地义。乡下的蚊虫多,师哥在蚊帐里睡得香甜,我在帐外被蚊虫疯咬,但我并不十分难受,我想师哥如果隔了帐子看我,我不是也在帐中吗?
不能同师哥建立甘苦与共的关系着实令我苦恼了好长一阵,虽然我牺牲了蚊帐和母亲送我的手帕,仍于事无补。学习不得要领的时候,师哥经常夸张地将我的败绩学给别人看。
我的师父是个善良的老人,团里的副团长,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他不像别人的师父那样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例如端尿盆一类。但是假如他要求,我一定心甘情愿的。
师父没有多少文化,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内秀而寡言,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戏人的神采,然而一到台上,他的周身便会散发出令人眼睛发亮的光彩。
关于他的事,我从不刻意记住,但是一想到那段日子,就必然想起他。于是,一桩桩一件件越发清晰,到今日竟成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师父只打过我一次。团里有一个长我们几岁的孩子,是个少年恶霸,欺负所有比他弱小的学员。大家敢怒不敢言,却暗下决心报复。一日他不在团里,我提议大家轮流往他的饭盆里撒尿,我先来,然后大家都来。那些人说:“好!”我于是开了先河,却再也没有第二个来续。当天下午便有叛徒告状,我自然得了应有的报应。他先打了我,又去找团长告状,我成了民愤极大的恶棍。他们哄闹着将我往厕所里推,要将我的头按到便池里,这时师父抢上前来踢了我几脚,接着大声训斥我。众人渐渐没了言语,师父的用意在平息众怒,使我免受更多的委屈伤害。
三
师父如此护着我,我却是他最没出息的徒弟,比如我艺术生涯中的首场演出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师哥作为后起之秀接过师父的衣钵,饰演师父之前的角色。而师哥先前的角色便过继给了我。我知道消息后失去控制地大喜过望,觉得卧薪尝胆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伸冤雪耻的时刻就要来了。我设法向我的两个弟弟“放卫星”,让他们到时来看我在台上如何大放异彩、光宗耀祖。
我饰演的角色在那出戏里无足轻重而且十分短命——上台后,我念完两句台词,就被周围的武士用刀剑胡乱“砍死”,就此我划时代的处女演出也就完成了。那是个没有姓名的角色,不会给人留下印象,仿佛是只为了这出戏的传统正宗而自然沿袭的一道程序,就像人的阑尾一样无关紧要,或者好比传统名菜里说不出名字也品不出味道的一种调料。
尽管如此,我还是砸了台。那天一出场,我就忘了台词。这一来,周围的武士们同仇敌忾,结结实实地对我刀剑相加。我绝望地趴在台上,任他们横砍竖杀,然后将“尸体”拖到后台。
我不知弟弟们是否认出了我,我暗暗希望他们干脆没来看戏。但师父一定因我出丑感到脸上无光。没过几天,他就得了疟疾,后来去世了,怀着对我的失望,这失望,因他生命的完结而变成不可更改的永恒印象。
我的第二个角色是在折子戏《程咬金打店》中演那个倒霉的店家。程咬金吃了饭却拒绝买单,非但如此还痛打了店家。这一回为防止悲剧重演,我做了充分准备,除睡觉之外,我总是默念着那几句性命攸关的台词:“忽听老客叫,慌忙就来到,上前拉住马——”
戏开始了,我立在幕边。程咬金在台上叫“店家——”
我身子虚飘飘的,“腾云驾雾”般上了台,做了一个拱手的姿态——老天,我又忘了台词!我拱手站在那儿,那一霎仿佛不知站了多少年。随后我头晕眼花,站立不稳,不是要向前栽,就是要往后仰。忽然间天外飞来的神示使我灵醒,上苍有眼,我脱口而出“慌忙就来到——”
这一句“慌忙就来到”从根本上拯救了我,否则这辈子我可能永远是个跑龙套的了。一心想成“角儿”的念头使我疯狂,使我绝望。我每天发狠练功,咬牙切齿,残酷无情,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
每个月我们每人有三十三斤粮、一两油、一两肉。我时常一顿便吃掉一天的定量。过度练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使我头晕目眩,“打飞脚”腾空跃起的时候经常失去平衡摔在地上。每个月总有七八天没有饭吃,整天躺在床上“挺尸”。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向时常能够得到家里接济的农村学员借地瓜干,掰成指甲大小,投进暖瓶“水发”。到下月初再用粮票偿还。如此寅吃卯粮,常有惊人的亏空。有一年到了春节光景,我彻底破产——除了一片带皮的熟肉,我没有一两粮票。那片肉是我的“年货”,春节期间的全部给养。后来有几个人饿得起不了床,根本无法练功。那几天剧团去外地演出,留下两个教师和十几名学员。我们饿得失魂落魄,练功时提不起精神,一招一式走了样,师傅就打我们。这下激起民愤,大家都不去练功了。
就在这年冬天,团里破天荒买了八斤豆子发给我和另外一个人作困难补助。这四斤豆子和那句“慌忙就来到”的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等值功效,它们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使我起死回生。那时我浮肿得厉害,眼睛成了一条线,总是睁不开。
时至今日,我仍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没偷没抢地活了下来。
四
1966年年初,正当戏剧改革、社教运动大张旗鼓之时,我意外地得到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穿着破旧的棉衣棉裤去医院看了父亲。不知为什么,父亲那天同我说了很多话,并嘱咐说:“你是老大,将来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而后父亲竟流了泪。那是我成年以后父亲第一次这样温和平静地同我谈话,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第二天中午,我突然心慌得不行。赶到医院,离探视时间还差二十分钟,守门人拦住我,我看着自己破旧的衣裳,羞于向他说明自己是李勇的儿子。无奈的我只好去街对面的书摊上花两分钱租了两本小人书,漫无边际地乱翻。我心中忐忑不安,草草看完,再奔到病房。
拐进那条走廊就看见父亲病房的门大开着,黑暗的过道上只有那一截映着白亮的天光,屋子里不断有人走动,慌张的影子在那截光亮处移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护士们在收拾器械,母亲和弟弟们在床边抹眼泪。
父亲的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脚上穿着灰色的尼龙袜子。无限的空虚惊愕中,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种想法:“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这想法如不祥的咒语一般套住我,同时我又希望它仅仅是一个咒语。我不眨眼地盯着父亲的那只脚,全心全意地希望那只脚会微微地动一下。
我伫立良久,没有人发觉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不接受那个事实。每个门里都有人安静地休养,只有那扇敞开的门里有一个永远睡去的人。没有人能够吵醒他,惹他愤怒生气,他也不再需要安静。无论怎样央求呼喊,他都听不见了,他沉入到永久的安静中去了。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一直对之忤逆不孝的父亲。
叔父们相继到了徐州。追悼会上,主持仪式的官员念着悼文,我发觉自己对父亲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我哭出了声,将眼泪鼻涕抹到破棉衣的里层。那一夜冷而清朗,我们都醒着不睡——除了父亲。我们要守着他,从天黑坐到天亮。
叔父们围坐在一起,说父亲从前的事。父亲年幼的时候英俊标致,远近闻名。逢年过节是乡村最热闹喜庆的日子,父亲因为扮相俊俏,嗓音脆亮,总被选去演社戏。父亲常扮旦角,他仿佛真是个穿戴齐整、英姿飒爽、光彩照人的女公子。爱热闹的壮年汉子们把父亲当作金枝玉叶扛在肩上,从这村到那村。父亲嘹亮脆嫩的高音在乡村神秘的夜里响着,传出老远。唱过大半夜,父亲还一直受宠地骑在别人肩上,脚不沾地。
父亲曾经也是稚嫩可爱的孩子,父亲还曾经那样迷恋唱戏。此时我觉得自己跟父亲陌生却极度地亲近着,胸中涌着无限的感激和怅惘。然而在我的心离父亲最近的时刻,父亲却远远地退避了,退到我超越不得的另一重世界去,我有无尽的话却只能作无言的冥想。
我依稀记得徐州的家里有一把胡琴,寂寞地挂在墙上,好像从来没人动过,我猜那应该是父亲的。
父亲去世后,我时常怀着强烈的思念,渴望以我和他之间特有的一种方式与他亲近。在想象中我听到那把胡琴咿咿呀呀的声音渐渐近了,是旧戏里的曲调,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父亲不老也不年轻,平和无言地看我。我想这便是我们父子间最温和最理想的对话方式。在不知名的熟悉曲调和冷旧的氛围中,我同父亲达成和解。由于内心的渴望,我在想象中不断完善着这情境。
父亲去世后我搬回家住,真正意识到长子长兄的责任。我逼小弟弟认真学画,经常因他完不成我布置的计划而责罚他。直到有一天我再也打不动他,他长成了大人,不再小姑娘似地听话。他身材魁梧,足足高我十公分。五兄弟里,我同他的相貌酷肖。他无疑是聪明有灵气的,不费什么力便考取了一所大学的美术系。那时候我已经在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了好几年。
1978年我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我拼上所有的力量,没日没夜地煎熬自己复习功课。考试的那个星期几乎没睡过像样的觉,考试时全身麻木几近虚脱。
更长更难耐的折磨是考试后的等待。我仿佛再也经不起失败挫折,大病一场,高烧不退。一直到八月底,通知来了,当天下午我的病竟然好了。
1985年我拍电影《流浪汉与天鹅》时路过徐州。当时母亲生病,准备住院,小弟决定去新疆写生。我们谁都留不住他,母亲也一样无能为力。他出发的那天,母亲住进医院。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小弟在新疆出了车祸。跟他同去的人说,在新疆他跪在戈壁沙漠对着漫漫黄沙放声痛哭,仿佛回应着冥冥之中神灵的昭示。
第二年,一位亲戚对我说:“你们哥俩都太要强了,你弟弟是让你逼死的。上天注定了你们俩只能留一个,也只能成一个。”
我回想自己对小弟的苛责大致同父亲对我的严厉不相上下。亲戚的这番分析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人——我师父和我父亲。
从那以后我心里长久充斥着不散的疑惑。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使我受到重创和长久负疚的折磨。师父的死让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脆弱,灵魂离开肉体的过程至今历历在目。父亲的死逼我磨砺自己,成就事业,以告慰他长眠的遗憾。而小弟的死,使我已经不年轻的生命又负载了他留下的使命。
难道仅仅因为要成就我,上天才从我身边夺去这些我深爱的人吗?难道仅仅因为要成就我,上天才让我承担这样沉重的负载吗?如果是这样,我值得这些人为我将自己的生命交还上天吗?如果是这样,我将做出怎样的成就才足以报偿这些人的牺牲?
痛苦焦灼的我常常因这样的追问而彻底堕入迷茫,但是没有谁能为我作答,我只有以我剧中人的悲喜哭笑作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停止。上天有知,他们的亡灵有知,我虽卑微平凡,却要尽毕生的力。
我久久铭记着法国荒诞派戏剧家科克托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粗糙的大理石坯,造化这个大师用锤子、凿子不断地敲打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忍受,不要呻吟不要哀嚎。配合他的敲打,因为他要成就你、创造你,去掉多余的,保留艺术必需的一切。”
岁月是刻刀,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每当我失望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上苍的目光在深切专注地对我凝视,那正是他最钟爱我的一刻。我将盛着满心的感动迎接这一切,报答这一切。